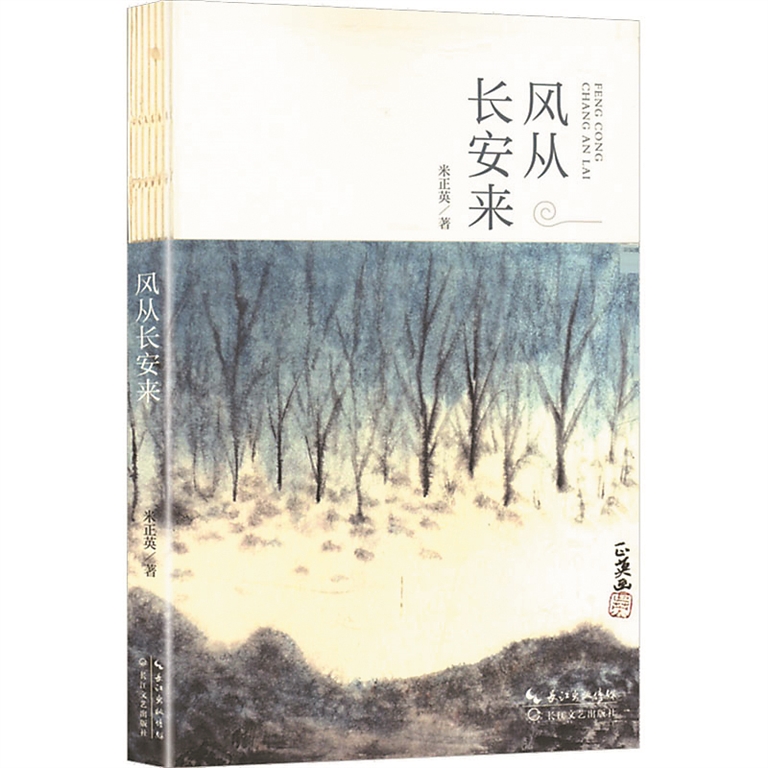
《风从长安来》/米正英/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6月
□杜波
江苏女诗人米正英的诗集《风从长安来》,以其对生命、灵魂、故乡与日常经验的深度开掘,呈现出时光鳞片般的多重面相。她将鲜活的记忆、具象、绘画的身体感受与深邃的灵魂探索熔铸于诗行,于平凡日常中彰显非凡的诗意。其诗歌意象独特,镜像丰富,景象动人,将乡愁文学的书写推向新的高度,文本中的女性映像和深刻的洞察力中展现出了独特的东方韵味和中式古典美学。不仅如此,米正英的诗歌亦有席慕蓉老师的诗风,其心有万象的绘画追求也亦相同。
意境:诗歌映像与乡愁重构
米正英的诗歌创作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记忆拓扑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历史与当下、地理与情感形成了复杂的量子纠缠态。她的《雨落长安》《风从长安来》《水意江南》等作品,将传统乡愁解构为具有流体特性的情感载体,在诗歌语言中实现了时空维度的突破。
在《雨落长安》中,“雨水顺着盛唐的屋檐/挂下来是星星”这一意象群完成了三重诗学转换:首先,雨水作为时间溶剂,将凝固的历史建筑溶解为流动的光;其次,屋檐这一物质实体在诗性观照下发生了相变,转化为星群的能量形态;最后,线性时间在液态介质中形成莫比乌斯环式的记忆褶皱。这种转化不仅呼应了齐泽克的“实在界入侵”理论,更创造性地将拉康的“对象a”概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诗学实体。星雨意象既是历史创伤的结晶物,又是未来可能的胚胎形态,在诗歌中形成了时空的量子叠加态。
米正英建构的“文明对流系统”呈现出独特的液态特征。长安作为文化中心,其历史势能在《风从长安来》中表现为“上古奇风”的动能;江南水系则构成引流的镜像,在《水意江南》中形成运河脉络般的记忆引导。二者之间产生的文化渗透压差,促成了持续的文化粒子交换过程。而“瘦成扬州桥头的冷月”这一意象,正是盛唐文化元素在江南溶剂中的溶解态呈现。这种双向渗透机制,使乡愁从单向度的情感投射转变为具有特性与个性的使命感。
当《母亲之诗》的“瓜熟蒂落”隐喻展现出更深层的生命拓扑学。脐带与瓜蒂在微分同胚意义上形成等价关系,这种分离过程释放的势能转化为诗意的辐射。果实包含的种子成为跨代际的记忆载体,而“蒂落”时的情感带有“行动诗学”意义的诗作创作也是作为作者对故乡以及江南的精神回馈与文化致敬。
意象:人性情愫中的情感脊梁
米正英的诗歌在情感表达上呈现出独特的人性质感与当代性特征。在《风从长安来》中,“人生仅有的一次旷世孤独交还给你”这一诗句将抽象的情感体验物化为可交割的文物,孤独被赋予青铜器般的物质属性——既具有考古学的历史厚重感,又具备艺术品的流通价值。这种情感物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代人际关系中情感商品化的诗性抵抗。
诗人通过“上古奇风”与“恍惚江南”的意象并置,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重组。汉唐风骨的刚性元素与江南水韵的柔性特质在诗行中形成的融合,创造出新型的情感升华。这种文化嫁接在《写回长安》中达到极致,高铁时速980公里的现代性体验,将传统乡愁的舒缓节奏压缩为数字时代的比特流,在速度与眩晕中重构了文化记忆的存储方式。
而《省略》一诗中“骨骼、火焰和刀锋”的意象组合,更具有“杀伤力”。这些冷兵器般的语词直指中年困境的本质,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剖开生命表层的伪装。而《蓝》中“用蓝手绢擦拭心灵直至透亮”的意象转化,则实现了色彩从视觉感知到精神信仰的升华过程。蓝色不再仅是视网膜接收的光波频率,而成为灵魂的防氧化涂层。
米正英的诗歌语言具有金属锻造的工艺美感:既有青铜铭文的古朴质感,又包含特种合金的现代强度。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为当代汉语诗歌注入了新的硬度和韧性,在保持诗意柔韧性的同时,建构起足以支撑现代人精神重量的情感架构。
意深:哲思的求索与艺术的跃升
对于诗人来说,想象力和现代汉语充分的化学反应,是他们进入现代诗歌的第一要义。
在《梦中,我从我的墓前经过》中,“死亡是生命的超越与升华”的宣言将“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转化为可体验的诗意场景。这种对于死亡的书写不仅超越了传统哀悼诗的范畴,更转化为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哲学思考。
《没有父亲的田野》这首诗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充满生命张力的乡愁图景,文本中的“空旷”作为核心意象呈现为克莱因瓶式的心理容器——田野的物质性空旷与记忆的精神性充盈形成非欧几何的情感褶皱。父亲的缺席被物化为负形雕塑,其存在感恰恰通过田野的虚空形态获得超验性确证。喇叭花的生殖力与母亲的衰老构成的生命悖论,延伸了具体乡愁。
在色彩方面,《蓝湖》中“将蓝湖高举至深处”的仪式,实现了从物理光谱到精神图腾的质变:蓝色波长在550至490纳米区间的电磁振荡,被转化为具有救赎功能的信仰图景。而《绘画记》的“青瓷笔洗”则构成一个微型宇宙模型:釉面开片模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盛放的光芒对应创世大爆炸的残余能量。这种大胆的“假设”让诗歌更具有张力。而最具革命性的是其留白哲学。《在一幅画中停顿》通过拒绝完成的姿态,建构了接受美学的极端案例:未画之鸟形成的“负形”比实体更具艺术性,这是艺术创作从单方面输出转变为双向的精神合谋。
意重:千年长安抒情的文明坐标
米正英在现代抒情诗传统之上,完成了时空维度的纵深建构,将单向度的乡愁怀想升华为多维度的文化记忆图谱,这既体现为一种诗性的传承,又呈现为更具深度和活力的创造。比如文本中拓展为“长安(历史)、江南(地理)”双向流动、互渗的文明对流系统与精神质地,都是在提取记忆中对自己的个体经验进行扩容、拓展,以形塑常态性的诗意内在发生机制。以青铜的冷峻孤独置换丝绸的古典柔情;以直面生死的存在锐度软化温情脉脉的生命牧歌;以艺术信仰让色彩从被凝视的唯美对象,进阶为承载神性体验与精神仪轨的媒介而多维地跃升。
当《风从长安来》的诗意之风吹皱江南水系,那“波光潋滟正向南方聚拢”的,不仅是盛唐的悠远遗韵,更是汉语诗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接通古老文化脐带的执着努力。这些诗作既源于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又凝结着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她的诗笔,兼具《绘画记》中“青瓷笔洗”的古典温润与《隐藏》里“深埋黑暗的黄金”般的现代锐利密度——这正是千年长安的雄浑气魄与烟雨江南的灵秀肌理共同孕育出的诗歌生命体。那些被风带来的“隔世琴音”,正是文化血脉在当代诗行中强劲搏动的胎音,还保持着泥土般质朴的质地,又在素简的意象森林里培育出丰饶的审美果实,是冷暖交织的人间烟火与永恒叩问的生命哲思,更是米正英诗学最富震撼力的当代回应与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