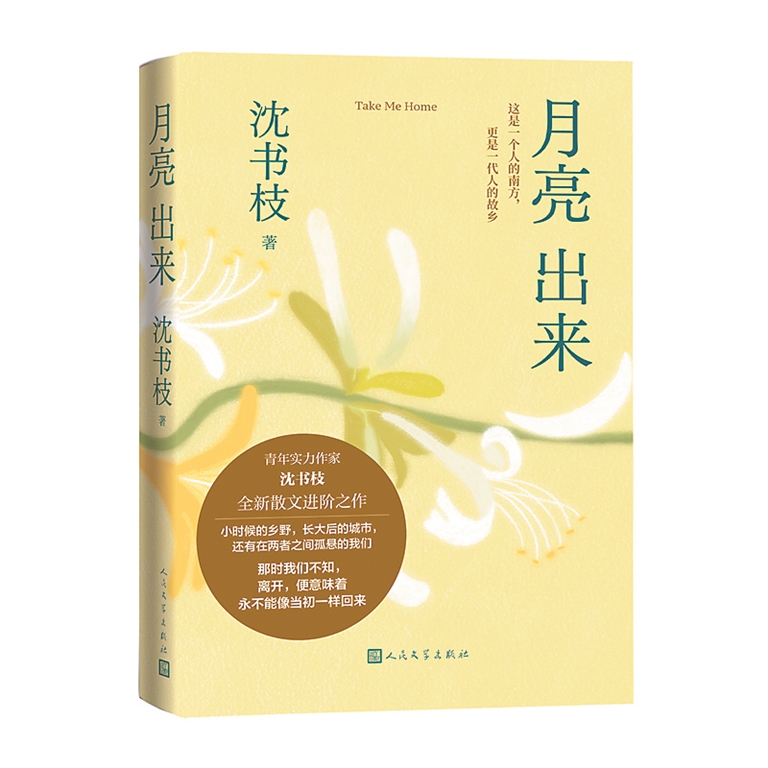
《月亮出来》/沈书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7月
□王咏梅
《月亮出来》书名取自山村暮鸟的短诗:“忽地/月亮出来/山丘之上/慢慢慢慢地走/谁在走”,诗篇中流淌着既温柔又诗意的画面感,潜藏着游子的羁旅乡愁。一草一木,一菜一汤,在沈书枝笔下的皖南乡愁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心中的江南”,更是一代人月光下的故乡。
“客居北京,每当三月将尽,清明在即,心中念念在兹的,是家乡的蒿子粑粑、映山红与蕨菜……”翻开沈书枝的散文集《月亮出来》,延续了其对故乡这一写作主题的执念,却在呈现上有了更为复杂的时间纵深与情感层次。书中敏锐地捕捉到当代人离开故乡后的“精神漂泊”,成为游子们人生羁旅的集体记忆。
《月亮出来》在作品表述上不乏特色:沈书枝的文字,最震撼人心的特质在于对细节的描写。当她描写故乡食物时,不厌其烦地铺陈制作流程:“锅里热油,下腊肉丁熬出油,下切碎的蒿子,下蒜苗,略略翻炒过后,加盐、加热水,最后加入已对半掺好的糯米粉和黏米粉,然后用锅铲用力揣拌均匀。”人间烟火气,看似家常闲话,却在文字律动间道出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在《乡下的晨昏》中,她写栀子花:“乡下用一种蓝边大碗来养它,从塘里或井里舀了水,把栀子满满地插一碗,放在房间的长桌子或木头窗沿上,夜里花香也是这样飘过来……窗子外面田里青蛙和鸣虫的声音起来了,灯灭下去,月亮一点点把光洒过窗子,又一点一点撤出去。”短短数行,由视觉、嗅觉、听觉交织成多维记忆空间,此处的月光,更赋予日常生活场景以“诗意的永恒”。
她在描写植物时极具张力:木槿花宛若“绢纸”,栀子花“展开如酒卮”,广玉兰有着“油亮的椭圆形革质长叶”。这些描绘既体现其入微的观察,亦有其独特的审美情趣。她写道:“植物所惠予我的,委实良多,好比儿童时代门口水塘里所生长的萍蓬,到如今仍年年在同一位置开出油亮的黄花。在过去经验之根系与今日经验之花叶之间,有细细茎秆埋藏于水下,默默将其连接。”“细细茎秆”的隐喻,则揭示了沈书枝对“乡土乡音”的深情眷恋。
书中对儿童心理的刻画堪称独到,沈书枝擅长捕捉那些“不足为大人道的乐趣”:孩童特有的感官敏锐度在文字间流动——看鼠曲草拉出柔软细长的白毛时的惊奇;冬日里因楼梯间冷清的簟子而莫名难过;伸手触摸母亲刚纳好的鞋时的温暖触感……这些描写让读者瞬间回到返璞归真的儿时记忆,将瞬间之美与永恒乡愁并置,唤起读者对生命中那些美好时刻的共鸣。
与沈书枝早期作品相比,《月亮出来》的突破在于对故乡“滤镜”的勇敢突破。在描述父辈生活时,她洞察到那些被忽视的情感需求;她体味出父母聚会时的絮叨背后,是对情感认同的深切渴望;她理解父亲“种田像绣花”其间蕴含的珍视与守护。这一崭新视角,使她的乡愁超越个人情感抒情,而成为一代人精神迁徙的见证。
《月亮出来》虽堪称当代散文的佳作,尤为可贵的是,书中乡愁的反思:既望向童年的南方故土,也审视着当下异乡人的生存状态;既怀念乡村的纯朴温暖,也不回避其局限与矛盾。这种辩证视角,使作品超越了一般怀旧散文的格局,成为记录中国城乡变迁的记录。不足之处是,一些细节描写稍显赘述,带来阅读上拖沓之感。
“用自己所能有的方式做一些事情,也许也包括记下它们,便是完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沈书枝笔耕不辍,在记忆河流中追寻似水流年,那些难忘的人与事。当读者随她的文字,漫步于月光笼罩的皖南山丘,触摸到那些带着露水的草木与乡村美食,乡愁被具象化为可感可知的“无处投递的思念”,提醒我们回望那些积淀成为生命底色的来处。
